京东七鲜过六一:全家童心30分钟达 618价格持续击穿!
京东七鲜过六一:全家童心30分钟达 618价格持续击穿!
京东七鲜过六一:全家童心30分钟达 618价格持续击穿!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xīn)技术与文化的快速融合(rónghé)发展(fāzhǎn),数字文化经济快速崛起,文化产业进入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如何抓住机遇,在全球文明变迁中实现数字文化引领,是中国面临的时代(shídài)命题。
一、 数字文化新业态(yètài)创造出文化产业发展的跃升
(一)数字文化新业态属于新质生产力。文化新业态是(shì)与传统文化业态相对的概念,一般是指新(zhǐxīn)历史(lìshǐ)条件下(xià)文化所(suǒ)呈现出新内容、新形式、新模式的总称[1]。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大批(dàpī)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包括数字音乐、游戏电竞、数字出版、MCN(多频道网络(wǎngluò)传播)、沉浸式体验等。它们以在线、智能、交互、跨界为主要(zhǔyào)特征,推动了要素重构、内容再造、传播加速、流量升级、价值创新和普惠民生。人工智能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是数字文化新业态最重要的特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wèi)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xiǎolèi)[2]实现营业(yíngyè)收入 5.24万亿元(wànyìyuán),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7.1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0.9%,文化产业已从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对滞后部门转变为先进(xiānjìn)部门。
(二)数字文化新业态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影响。首先,数字文化新业态是“文化+科技”的现代化表现形式(biǎoxiànxíngshì)。“文化+电力”产生了电影(diànyǐng)和电视,“文化+互联网”产生了网络文艺、网络游戏,这些都是“文化+科技”的产品,而(ér)“文化+人工智能”则产生飞跃性的变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人类文明进入新形态的重要标志,其产生的文化产品,催动(cuīdòng)文化产业发生(fāshēng)巨大变化(jùdàbiànhuà)。
其次,数字文化(wénhuà)是(shì)新时代的增量文化,是文化流动的产物。随着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的横空出世,文化流动与文化信息处理,有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量。人工智能训练规模的增长速度是大约每2年增长15倍(bèi),以ChatGTP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则是每2年750倍的增长速度[3](马占凯,2023)。数字文化新业态不仅加速了海量(hǎiliàng)文化要素(yàosù)的自由流动,还将更加便利(biànlì)地(dì)实现文化要素的自由组合。旧元素的新组合,正是熊彼特所指的创新,也必然带来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其三,数字文化改变(gǎibiàn)着(zhe)文化产业链的全链条,全球文化价值链正在加速调整(tiáozhěng)。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交易、智能推广等算法、软件、硬件(yìngjiàn)和平台(píngtái)层出不穷,改变着文化的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的全链条。抢占数字文化价值链高地和数字文化价值分配权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识。
其四,科技与创意高度融合,赋予人类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wénhuà)内容。借助人工智能的利器,每个人不仅是(shì)文化成果的享有者,而且能成为创造者。数字(shùzì)文化前所未有的释放全民创意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数字文化内容形态向网络文学、数字游戏、3D虚拟影像等演变催生出新兴内容创作(chuàngzuò)生产者(shēngchǎnzhě)群体,形成庞大的新兴内容市场(shìchǎng)(shìchǎng)。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海量内容生产,成为新兴内容市场的核心支撑,产生巨大市场价值。数字文化兼具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四种文化特征,必将促进城市(chéngshì)文化的繁荣,并引领城市文化的未来。
(三(sān))数字文化(wénhuà)新业态正构建世界文化产业(wénhuàchǎnyè)新格局。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技术的快速发展(fāzhǎn)已经深刻影响到文化各个领域(gègèlǐngyù)。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欧洲的一些地区加快部署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抢占文化科技、数字文化规则、数字文化市场等制高点和话语权。中国依托市场规模大、应用场景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与人工智能发展后来居上的优势,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一是(shì)数字(shùzì)文化市场正在成为全球(quánqiú)文化主流市场。文化产品(chǎnpǐn)如(rú)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等已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产品通过电影院、音乐流媒体、图书出版和在线平台等渠道,在全球范围(fànwéi)内被广泛传播和消费。以数字音乐为例,数字音乐成为国际音乐产业贸易的强劲引擎。由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发布的《2024年全球音乐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录制音乐市场价值286亿美元,其中,流媒体收入增长是主要驱动力(qūdònglì),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7.3%。
二是形成了“全面(quánmiàn)发展”和“特色发展”两种(liǎngzhǒng)数字(shùzì)文化(wénhuà)新业态发展路径。美国硅谷是“全面发展”的案例。硅谷已经形成了大学—产业—政府—资本“四轮驱动”创新模式,催生了众多(zhòngduō)数字创意企业,成为数字文化产业(wénhuàchǎnyè)包括新型企业、新型业态、新型模式集中诞生地。英国伦敦(lúndūn)(lúndūn)是“特色发展”的案例。根据伦敦创新署的一份研究报告:2016年至2021年间伦敦沉浸式科技公司吸引的风险投资高达10亿美元,为欧洲之最;伦敦的VR和AR使用量占全英的比重为33%;伦敦拥有215家沉浸式科技公司,占全英总数的48%。
三是(shì)“新主体”与“融合”成为数字(shùzì)文化(wénhuà)新业态关键词。一方面,数字文化平台、文化数据资源供给者、数字文化资本(zīběn)等(děng)新主体不断涌现,共同参与构建了新型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生态中,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媒体工作者等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de)合作,这种“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交叉融合”,把人文精神与技术开发相结合,持续创造出新产品和新业态。
二、 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fāzhǎn)重塑文化全链条
当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相遇,不仅产生(chǎnshēng)了(le)新的文化生产主体、客体、工具、方式(fāngshì),也产生了新的生产资料、消费方式、文化生态和文化治理,推动文化产业市场繁荣。
(一)人工智能产生新的文化生产力(shēngchǎnlì)
其一,“智能体(tǐ)”成为部分文化生产主体的(de)“替代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shàng)成为内容生产者(shēngchǎnzhě),既可以人机合作的方式(fāngshì),也可以独立进行文化创作(chuàngzuò)。微软公司研发的能够写诗的人工智能“小冰”等,相当大程度上提升了部分产业的工作效率与产出效能,突破了弱人工智能技术可读性弱、逻辑不严密、互动性差(chà)的固有缺陷(quēxiàn)。2017年DeepMind团队宣布阿尔法狗(AlphaGo)退役(tuìyì),同时公开了50盘AlphaGo自我对弈的棋谱,这50份棋谱正是智能体所创作或生产的。2024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有四部全部用人工智能创作的长篇小说销售,竟然一书难求。
其二,AI创作(chuàngzuò)工具成为人类创造力帮手和创意引擎。无科技不文化。AI工具正在成为新的(de)(de)文化生产工具,帮助创作者自动化辅助、提高效率(tígāoxiàolǜ)、改善创意。越来越(yuèláiyuè)多的人通过Midjourney、Suno AI、ChatGPT等平台(píngtái)自动生成创作AI绘画、AI音乐、AI文章等作品。2022年8月底(yuèdǐ),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bólǎnhuì)艺术比赛中(zhōng),一副名为《太空歌剧院》的作品获得“数字艺术/数字修饰摄影”类别第一名,而这幅作品实际上是用Midjourney协助创作的。2024年深圳南山(nánshān)基本操作科技公司的AI时尚设计“LOOK”系统,帮助乌克兰基辅博物馆将已逝的服装设计师的设计手稿AI呈现,做成了真实服饰进行展览,还做成手办销售,让艺术不再(bùzài)有遗憾。
其三,数据和数字资源成为数字文化创作的核心(héxīn)(héxīn)要素。以数字数据作为核心要素,依托“数据+计算力”,促进了(le)数字文化产业链(chǎnyèliàn)上下游、产供销协同联动,推动了数字文化产业场景开发(kāifā),提升了文化生产力水平。“云游敦煌(dūnhuáng)”线上总访问量远远超过敦煌莫高窟的年接待量,丰富了文化旅游活动体验,为艺术探索增添了新的方式。湖南博物馆通过高清影像(yǐngxiàng)拍摄和激光扫描等(děng)手段,采集文物(wénwù)数据103万条、图片11万张、三维模型2000个,推动构建(gòujiàn)马王堆汉墓文物、音乐文物等文物知识图谱,形成数字文化资产,加快“数字汉生活”文化IP开发。2022年8月,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正式上线“全国文化大(dà)数据交易中心”,通过“数实结合”的方式,孵化了黄金首饰珠宝名表、文化艺术品、文化大数据应用交易等10多个文化垂类(chuílèi)细分领域交易子平台,正在构建出版类、音视频(yīnshìpín)类、IP玩具、茶叶类等细分垂类行业子平台。近一年来,累计(lěijì)总交易金额达300.09亿元。
(二)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催生新的文化生产方式
首先,数字(shùzì)(shùzì)文化新业态实现了“长尾力量(lìliàng)”的文化生产方式。“长尾理论(lǐlùn)”是指“聚沙成塔”的小批量多品种生产,销售成本越低,销量就越大。长尾有三种力量:制造它,传播它,帮助我找到它。人工智能技术通过(tōngguò)(tōngguò)生产工具(gōngjù)(shēngchǎngōngjù)的数字化、让消费者同时成为传播者、降低搜索成本推动“长尾力量”转化为生产力。生成式人工智能让文化生产工具“大众化”,让每个(měigè)人都可以使用专业的工具。每个人获得(huòdé)数字文化资源的可能性、便捷性大大增加,通过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文化资源要素组合的便利性提升,通过个人私域和公域进行传播的方式更多元。如前所述,每个人既是数字文化的消费者,又是数字文化的生产者,还是数字文化的传播者。
其次(qícì),数字文化(wénhuà)要求同步推进文化软实力与硬(yìng)实力。文化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生产经营传播文化产品和信息产品的产业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文化产品实现市场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任何人都能成为“作曲家”,作曲软件(ruǎnjiàn)可以帮助(bāngzhù)人们在几分钟内创作出一首歌曲。2024年(nián)自称“对(duì)音乐一窍不通”的作家冯唐,借助腾讯音乐启明星平台的AI技术谱曲、演唱,推出个人首张AI创作专辑《A爱》,这也成为全球首张诗人AI歌曲辑。
(三)人工智能产生新(xīn)的文化消费方式
其一(qíyī),数字(shùzì)文化平台(píngtái)兴起,消费方式和(hé)(hé)分配方式革新。消费互联网已经成为(chéngwéi)新型的(de)社会(shèhuì)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发生和完成的。数字平台的丰富多彩,提供了(le)极大的创意展示价值(jiàzhí)和营销途径。火爆的抖音、快手造成了现象级的全民创作热潮,抖音平台还融入了“直播+带货”和“短视频+直播”模式(móshì)。这种模式与快递业务结合,推动了线上消费的蓬勃发展(fāzhǎn)。平台模式从“送文化”进化到“营销文化”,消费者从“用脚投票”转变为“用手投票”(点击转化率)。数字文化平台正在成为信息撮合载体、产品交易媒介、文化传播公共空间,助力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4](杨云霞、张宇龙,2021)。同时,数字文化平台也在改变着文化价值链的分配方式。基于数据要素资源和算法的优势,文化产业互联互通对全球文化产业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其二,数字文化出海,让全球(quánqiú)消费(xiāofèi)者为(wèi)文化品牌(pǐnpái)买单。发展数字文化消费是打造国际消费中心的重要方式。互联网、数字流媒体服务(fúwù)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文化产品跨国传播的成本和难度,使得全球消费者能够即时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shìjiègèdì)的文化内容。首先开始的是文化内容的全球传播,包括李子(lǐzi)柒美食短视频等迅速(xùnsù)走红(zǒuhóng),《黑神话:悟空》游戏等爆火全球。在美国(měiguó)一些网络社区,玩家热烈地讨论(tǎolùn)着不同语言版本的《西游记》,在玩游戏之前先来一次“文化速成班”。其次是数字文化平台的出海,以抖音海外版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带动整个平台生态进入海外市场。在网络游戏海外市场,中国移动端游戏弯道超车,2024年自研游戏海外市场收入美、日、韩占比分别为31.06%、17.32%、8.89%。[5]
其三,丰富的(de)(de)数字(shùzì)文化(wénhuà)(wénhuà)中间产品拉长、壮大了消费链。数字文化产品既是(shì)产品也是文化数据要素或中间产品,因此数字文化产品再创作相对传统产品更为容易,加速壮大文化消费链。常见的再创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文化产品的横向全方位开发,从网络文学到动漫、游戏、电影、连续剧、文旅、周边产品开发等(děng),形成(xíngchéng)围绕IP的数字文化产品矩阵。深圳华强方特围绕“熊出没”IP部署了动漫、电影、乐园(lèyuán)、周边等系列产品。另一种方式是数字文化产品的纵向“接力棒式”创作,数字文化的消费者也是数字文化的生产者,消费数字文化的同时,通过对数字资源的再创作,形成新的数字文化产品。这种方式在(zài)短视频领域颇为常见。
(四)人工智能重构文化生态(shēngtài)和新的治理方式
首先,文化事业和(hé)文化产业的界限进一步模糊。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宝藏,数字技术让它们更加鲜活(xiānhuó)。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事业可以(kěyǐ)形成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也可以通过文化市场来实现,两者的不再泾渭分明。故宫博物院(gùgōngbówùyuàn)等文博(wénbó)单位利用大(dà)数据建设“数字博物馆”,开发线上小程序,将古董文物移到网络,建立数字馆藏,产生数字文博、展览等新业态,让消费者可以异地进行(jìnxíng)参观和消费,提升了体验感受。
其次,数字(shùzì)文化生态重构新型数字文化生产关系。与传统文化生态以企业为核心(héxīn)建立(jiànlì)不同,数字文化生态是以数字内容(nèiróng)平台为核心建立的多主体(zhǔtǐ)交互关系结构,数字内容平台既是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建构主体,也是各方主体的联结者和服务者[6]。在数字平台上,不仅有大量注册的消费者,还有(háiyǒu)大量注册的某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名人、明星、网红等,数字平台还与政府部门、大数据服务商、中介服务机构(jīgòu)、商家(shāngjiā)、社会组织(zǔzhī)等存在双向的合作扶持关系。数字平台、AI智能体、文化数据要素市场等都是数字文化生态的新元素,平台治理、数据市场构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文化伦理、数字文化国际规则制定等成为数字文化治理的重要新内容。更(gèng)重要的是数据算法取代了原来群体力量(lìliàng)协调关系,从而大幅降低了协调成本。[7]
三、 中国文化业态演进及数字(shùzì)文化新业态布局
我国(wǒguó)数字文化上市(shàngshì)企业数量位居全球之首,截至2024年底,我国(含港澳台)数字文化新业态领域共有上市企业881家,日本数字文化上市企业608家,美国数字文化上市企业467家。[8]中国在几十年里(lǐ)将科技革命中的电力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与文化发展进行深度融合,走出了全球文化创新性(chuàngxīnxìng)发展的新路(xīnlù)。

(一)从“文化+科技”看中国文化业态(yètài)演进
在(zài)人类文明史上,文化与科技一直相伴(xiāngbàn)互生、相互促进。科技的发展为文化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文化繁荣诞生的新观念和新的艺术形式表达为科技在文化领域的应用(yìngyòng)、传播提供了土壤与环境。按照“文化+科技”的视角,可以将中国(zhōngguó)文化业态演进划分(huàfēn)为四个阶段。
一是“文化(wénhuà)+电力”时期。1998年之前都处于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文化装备(zhuāngbèi)制造能力的发展,文化生产(shēngchǎn)机械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不断深化。文化创作依然在线下,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是艺术家(yìshùjiā)和工人,劳动对象是文化出版物和文化装备,劳动工具是机械。文化流动还(hái)依赖于人、唱片、影碟等物理载体。
二是“文化+互联网”时期。1998年前后,网易、搜狐、新浪(xīnlàng)、腾讯四大门户相继成立,带来了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电影、在线音乐等的(de)(de)快速发展(fāzhǎn)和繁荣。文化创作和生产(shēngchǎn)的线上化,加速了文化资源(zīyuán)数字化。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是专业创作者,劳动对象集中在数字内容,劳动工具更多采用了信息技术。文化流动摆脱了物理载体的限制,网络社区成为文化流动的新型载体空间。
三是“文化+移动互联网”时期(shíqī)。2011年微信的(de)诞生代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2012年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进入全球视野(shìyě),2017年GPT人工智能诞生,都意味着这段时期是移动互联网和(hé)传统人工智能交互发展的时期。智能手机加速了手游(shǒuyóu)、短视频、动漫等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传播数字化加速。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拓展到了爱好者,劳动对象转向移动端文化产品,劳动工具更多采用移动信息技术。文化流动带来的数据(shùjù)资产被用来转化为成短视频等新的文化产品,“转化”成为(chéngwéi)文化流动的新特征。
四是(sìshì)“文化(wénhuà)+生成式人工智能”时期。2022年(nián)底ChatGPT正式上线并商业化应用,2023年OPENAI、蚂蚁集团、科大(dà)讯飞、谷歌、微软、英伟达、百度、腾讯等共同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国际标准。2024年DeepSeek发布并开源,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文化新观念和新艺术形式(xíngshì)表达(biǎodá)实现了“双轮”平衡发展。激发了全(quán)民族(mínz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中国文化发展迎来“新大众文艺”时代,科技赋能(fùnéng)打破了创作壁垒,文化权利重新分配,全民皆可创作、人人皆可传播(chuánbō)。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拓展到了智能体和“全民创意”,劳动对象向数据资产转向,劳动工具采用更多通用和垂类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了文化数字化全链条(liàntiáo)贯通发展,文化创意、生产、传播一体化周期大幅缩短,劳动工具前所未有的丰富。依托AI技术的文化要素的自由组合成为文化流动(liúdòng)的核心特征。
(二(èr))中国数字文化新业态的国际发展布局
中国数字文化新(xīn)业态活力持续迸发,具有特色领跑、全面布局的特点。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和网络游戏(包括(bāokuò)电竞)被称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中国网络文学已与美国(měiguó)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称“世界四大文化现象(xiànxiàng)”。[9]
其一,网络文学(wǎngluòwénxué)成为中国IP出海(chūhǎi)最大源头。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guīmó)达430.6亿元(yìyuán),其中海外(hǎiwài)市场规模达到50.7亿元,海外活跃用户达到3.5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dìqū),以北美、日韩(hán)、东南亚为重点输出地区。以阅文集团为代表的出海企业加大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布局,人工智能翻译助力网文(wǎngwén)“一键出海”。近年来网文出海向IP生态出海升级,成为中国文化产品出海最大的IP源头。
其二,网络(wǎngluò)视频(shìpín)(shìpín)平台成为(chéngwéi)文化(wénhuà)全球化的重要载体。网络视频的出海包括中长视频、微(wēi)短(duǎn)剧和短视频。中长视频领域以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哔哩哔哩五大平台为主力军。微短剧于2023年开始爆发,包括中文在线的ReelShort、九州文化的99TV等。在短视频方面,TikTok(抖音国际版)、Kwai(快手国际版)、微短剧平台ReelShort等中国短视频平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其三,网络游戏迈入(màirù)全球前列。自2020年(nián)以来,我国网络游戏出海的收入规模连续5年超千亿元。2024年全球游戏市场(shìchǎng)总收入约1843亿美元,中国海内外的游戏营收总额(zǒngé)约643亿美元[10],占全球份额约35%,并出现(chūxiàn)腾讯、游科互动等游戏出海头部企业。腾讯旗下的《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等游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玩家(wánjiā)基础。
其四,数字文旅方兴未艾(fāngxīngwèiài)。在文旅融合(rónghé)基础上不断推动文旅数字技术与(yǔ)实体(shítǐ)经济的二次(èrcì)融合,数字艺术展览、全息互动剧场、智慧乡村文旅等新业态加速发展。中国数字文旅市场规模由2017年的7870.5亿元增至2022年的9698.1亿元,增幅达57.89%。
其五,动漫、电商等领域全球影响力逐步攀升。据统计,在播热门动画评分排名前60中,有13部中国(zhōngguó)作品上榜。在MCN和电商直播(zhíbō)方面,“直播带货”的经营模式和中国物美价廉的小商品传至海外。我国数字文化出海(chūhǎi)(chūhǎi)显然已由“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转型,并以跨境电商平台Shein等现象级(jí)平台成功打入海外市场。中国动漫电影持续(chíxù)发力,截至2025年5月,《哪吒2》全球票房已经(yǐjīng)突破158亿元,跻身全球前五。
(三)中国数字文化新业态的(de)主要城市格局
依据2023年(nián)各城市数字文化上市公司企业数量和规模,选择排名前4的城市作为(zuòwéi)分析对象(duìxiàng),可以发现,中国已经形成了差异化的城市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格局。
一是北京在装备、媒体、视听(shìtīng)等领域发展引领全国。2023年北京规模(guīmó)以上“文化+科技”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已经破(pò)万亿,拥有百度、联想(liánxiǎng)、小米等千亿级上市企业,以及快手、爱奇艺等直播与视频视听平台公司。2023年,北京数字(shùzì)文化装备类主要上市公司营收规模超6000亿元(yìyuán),位列全国城市(chéngshì)第一;媒体传播类上市公司营收规模超1600亿元,位列全国第一;网络视听类上市公司营收规模超1400亿元,位列全国第一;集聚了拥有数字文化基础技术的(de)上市公司61家,远超上海、深圳等城市。
二是上海(shànghǎi)网络文学和电竞(jìng)产业(chǎnyè)居全国领先地位(lǐngxiāndìwèi)。网漫、网文、网游联动发展,成为上海数字文化产业的(de)(de)重要新生力量。网络视听领域以(yǐ)哔哩哔哩为主力,网络文学以阅文为代表(dàibiǎo),网络游戏以米哈游为代表。社会科学院(shèhuìkēxuéyuàn)近期发布的《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2024)》显示,2022年上海网络文学实现了120亿元的销售收入,位居全国领先地位;网络游戏产业更是实现了1280亿元的销售收入,占(zhàn)全国总规模的三分之一;同时,上海电竞产业也表现出色,产值达到269亿元,赛事收入60亿元,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11]。新业态还带动了文化场馆、出版与印刷、演艺娱乐等(děng)门类的持续转型,成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头之一。此外,上海还是索尼、宝可梦等数字文化外商投资企业布局的主要(zhǔyào)城市,国际化特色明显。
三是深圳网络游戏位于前列,产业增速创造奇迹。深圳在数字文化装备、网络游戏以及网络视听三大领域(lǐngyù),拥有华为(huáwèi)、腾讯、华强(huáqiáng)等(děng)头部企业,实力(shílì)强劲。深圳集聚了全国最多的文化装备上市公司,文化装备营收(yíngshōu)规模(guīmó)全国第二(不含华为);2023年游戏领域上市公司营收规模超过30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dìyī);2022年至2024年雷鸟创新位居AR领域市占率第一。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科技”的产业发展新模式,出台(chūtái)国内第一个(dìyígè)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率先在全国推动“文博会(wénbóhuì)”构建数字文化市场(shìchǎng),率先试点建设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作为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之一,深圳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03年的135.3亿元,到(dào)2023年的超过2750亿元,20年增长了超过20倍;支柱性产业的地位不断巩固,文化产业增加值由所谓的“文化沙漠”跃升到全国最前列。
四是(sìshì)杭州以“游戏+视听”为引领,成为全国数字(shùzì)文化重镇。杭州网络视听领域以阿里(ālǐ)巴巴旗下的阿里文娱为主力,阿里文娱业务包括优酷土豆、阿里影业(yǐngyè)、阿里音乐、阿里体育、UC、阿里游戏、阿里文学、阿里数字娱乐事业部。2023年(nián),杭州视听领域上市公司营收超1200亿元,仅次于北京。杭州一直是游戏重镇,平均每个月就有20款网络游戏“杭州造”,网易雷火、电魂网络、游卡(yóukǎ)网络等(děng)众多国内领先的游戏研发企业在此集聚(jíjù)。杭州支持《黑(hēi)神话:悟空》等原创游戏通过Level Infinite等平台进入(jìnrù)海外市场,对版权授权收入给予最高50%补贴。2023年,杭州游戏上市公司营收超800亿元。
除了以上举例的(de)4个城市外,全国其他各省、区、市在近一两年,也在数字文化新业态(yètài)上各展(gèzhǎn)风采,创造出文化产业发展的奇迹,展示了中国在数字文化新业态面前的强大力量。
四、 发展数字文化(wénhuà)新业态面临的主要挑战
不同类型的(de)数字文化业态发展的具体问题虽然值得(zhíde)关注,但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面临的本质问题更值得探讨。本文以战略思维、全球视野(shìyě)探讨数字文化市场建设、价值(jiàzhí)创造、传播分配、生态体系的四个方面挑战。

(一)文化数据(shùjù)要素市场亟需提质升级
全球文化(wénhuà)竞争力比较的是文化产业竞争力,是市场(shìchǎng)决定文化资源要素配置的能力。数字(shùzì)文化内容形态向网络文学(wǎngluòwénxué)、数字游戏(yóuxì)、3D虚拟影像等演变催生出新兴内容创作生产者群体(qúntǐ),形成庞大的新兴内容市场。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海量内容生产,成为新兴内容市场的核心支撑,产生巨大市场价值。在全球市场规模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数量方面,我国还有提升空间。
我国是文化(wénhuà)(wénhuà)(wénhuà)资源大国,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亟需提质升级。数据要素是数字文化生产的首要要素,文化资源是文化产品生成的基础要素,吸收、整理、转化文化资源是进行内容创作的第一步骤(bùzhòu)。然而,与我国文化资源相比,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程度(chéngdù)还不高。中华文明经历了数千年的演进和发展,积淀(jīdiàn)了海量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数据散落在思想理论、文化旅游(lǚyóu)、文物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文化等(děng)不同领域和部门机构,它们以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呈现,处于或关联或分散的状态(zhuàngtài)。将中华民族积累五千多年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jùyǒu)文化内涵的数据,成为文化大模型训练(xùnliàn)数据,不仅可以补齐当下大模型训练数据短缺的短板,而且可以大幅提升文化机构的效率和效能。当前,文化数据要素市场的产权、准入(zhǔnrù)等基础制度尚未完善,公共文化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授权开发机制尚不明确,文化数据要素的交易规则(jiāoyìguīzé)尚待健全。
(二)数字文化(wénhuà)价值链仍需高端化
集中力量建设文化(wénhuà)(wénhuà)IP(知识产权)大国(dàguó)。我国文化产品(chǎnpǐn)出口稳居全球第一,文化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持续提升,培育了一批特定领域(lǐngy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de)文化企业、产品和品牌。同时,应该看到,相较于迪士尼、漫威等企业的IP集群,我国取得商业化成功的IP数量较少,我国影视、版权、创意设计等高附加值文化服务出口仍然较少,出海的文化产品还应加强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市场号召力。如何(rúhé)让全球消费者为中国高质量文化IP买单,是值得文化产业领域深思(shēnsī)的问题。
(三)智能算法有待(yǒudài)优化
一是文化消费(xiāofèi)革命加速了文化资源整合的(de)平台化发展(fāzhǎn)。在数字化、网络化(wǎngluòhuà)、智能化的当代社会,以新消费观念、新消费群体、新消费内容以及新消费场景“四新”为标志的消费革命,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结构(jiégòu)和(hé)走向。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影响着新经济形态下的产业发展规律,掌握海量(hǎiliàng)用户和数据资源的数字平台企业快速发展,数字文化各个细分(xìfēn)行业都由几大头部(tóubù)平台占有较高市场份额。数字文化平台企业依托强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海外投资、合作和并购等方式出海,搭建海外内容原创平台,运用数字技术探知和挖掘海外消费者的兴趣,培养稳定的海外受众,不断提升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二是要抛弃“算法歧视”和“算法霸权”。AI以算法为运行基础,改变传统以“传者”为中心的(de)国际传播话语范式[12],智能算法成为数字(shùzì)文化海外传播的隐形(yǐnxíng)操作者。企鹅智库有关内容创作目的调研报告显示,创作者收入(shōurù)的诉求最强烈,占比达到71.7%[13]。但目前网络创作者主要的收入来源,仍是平台侧流量变现的分成(fēnchéng),这意味着(yìwèizhe)海量(hǎiliàng)内容创作者中只有极少数粉丝流量高的创作者能获得可观的收入。[14]
(四)数字文化生态体系尚不(bù)完善
一是数字文化打破(dǎpò)“四个(sìgè)边界”加速文化流动(liúdòng)和要素组合。数字文化打破了(le)创作者身份、地位、头衔等(děng)层级驱动的垂直边界,打破了业务领域、职能和部门等带来的水平边界,打破了创作者与客户、供应商、社区等之间的网络边界,打破了地理市场(shìchǎng)之间及文化之间的距离边界。“四个边界”被(bèi)打破,让创意、信息、资源能够自由流动,提升了文化流动的速度、灵活度、整合效能和创新(chuàngxīn)效率,人人都可以在数字内容平台上发布创意内容,甚至直接参与专业机构的文化内容创作和产品(chǎnpǐn)生产,显著提升了全社会的互动水平、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激发了“全民创意”。
二是生态(shēngtài)竞争力(jìngzhēnglì)决定了业态繁荣,从而形成业态竞争力。新业态的(de)(de)发展更加依赖于数字文化生态。数字技术(jìshù)与文化产业“内容生产—传播推广—消费体验”全产业链条的深度融合,促使文化生态形成企业、创意阶层、用户、数字平台、相关政府部门等构成的多元市场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数字文化生态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用户价值,产品(chǎnpǐn)(chǎnpǐn)生产由链式转为多主体网络协同的并行式,产业生态组织形式从园区实体转变为基于数字技术的虚实结合集聚,数字技术创新催化内容产品持续迭代升级[15]。因此,需要构建集合数字平台、政府部门以及(yǐjí)中介服务(fúwù)机构、商家、社会组织,共同营造平台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配置政策、人才、资金(zījīn)、技术、信息(xìnxī)、数据、服务等要素,构建开放(kāifàng)融合、价值创造的数字文化新业态。
三是新型(xīnxíng)生态(shēngtài)倒逼文化转型升级,促进全过程创意“五链融合”。数字(shùzì)文化生态建设需要基于法治化,尤其是数字知识产权保护。2023年美国编剧工会和(hé)演员(yǎnyuán)工会纷纷罢工,以此争取对(duì)编剧知识产权和演员肖像权的保护,同年发布的《版权(bǎnquán)登记指南(zhǐnán):包含人工智能生成材料的作品》提出智能体生成品不受版权保护。数字文化需要与之匹配的劳动、资本等要素市场。中国人民大学(zhōngguórénmíndàxué)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超过65%的地区文化数字化创新水平与IT、科研等领域的复合型数字人才就业情况较为协同。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对资金产生庞大(pángdà)需求,需要懂科技、懂文化且投早投小的数字文化耐心资本。综合来看,数字文化生态的完善,必将形成(xíngchéng)文化产业链、版权价值链、科技创新链、文化资本链、数字人才链五链融合体系。
五、 促进(cùjìn)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的建议
站在全球文明演进和文化转型的(de)(de)历史节点,中国有望参与全球数字文化的塑形,推动全球现代文明的建设。
(一)将数字文化放置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de)高度开展顶层设计
一是(yīshì)推动(tuīdòng)中华(zhōnghuá)优秀传统文化(wénhu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fāzhǎn),推进中国(zhōngguó)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率先打造自信繁荣的(de)数字(shùzì)文化,虹吸(hóngxī)汇聚全球文化在中国与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型载体和表现形态,向世界准确传递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激发市场力量、大众力量,创造引领时代的数字文化观念。二是促进(cùjìn)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市场发展和繁荣。坚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文化流动理论为根,以文化技术创新为本,以促进全民创意为翼,以数字文化市场培育为要,以文化转型升级为目标,提升文化市场的主体活力、文化资源的转化力、文化内容的创新力和数字文化的传播(chuánbō)力,培育文化领域(lǐngyù)的新质生产力。三是支持全球数字城市文明典范和数字文化示范城市建设。一个国家和城市可以自觉地塑造(sùzào)数字文化。选择有条件的城市,授权数字文化改革试点,建设数字文化示范城市。
(二)发展数字文化的区域统一大(dà)市场和文化数据要素市场
一是(yīshì)在国家重要城市群推动数字(shùzì)(shùzì)文化(wénhuà)(wénhuà)(wénhuà)统一大市场(shìchǎng)。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探索推动区域数字文化市场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的设施高标准联通,要素资源市场与商品服务市场高效协同(xiétóng),市场监管规范公平统一,助力全国建设数字文化统一大市场。二是以(yǐ)市场的力量主导推动数字文化业态大发展。建设数字文化基础设施,依托实力雄厚(shílìxiónghòu)市场主体加速文化事业的市场化。着力培育龙头企业、平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中小科技型(kējìxíng)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梯队(tīduì)。重点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yǐngshì)、电商、娱用无人飞行器、可穿戴设备、数字文旅等数字新业态发展。三是培育发展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推动实施文化大数据战略,制定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的政策,鼓励培育文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市场规则,强化市场监督,以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shùzìhuà)战略的落地落实。统筹公共(gōnggòng)文化机构(jīgòu)有序供给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应用场景,坚持开放共享的观念,彻底打破“系统墙”“数据孤岛”,做大做强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开展文化数字版权资产交易,跨区域数据协调,公共文化数据资源开放等,探索RWA(现实世界(shìjiè)资产)的实现路径,加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数据资源和数据资本。
(三)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科技(kējì),提升数字文化产业原创能力
一是支持(zhīchí)文化(wénhuà)领域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文化数字技术创新。抓住文化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牛鼻子”及(jí)“弯道超车”机遇,大力(lì)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VR、AR和物联网等(děng)领域的(de)技术在文化领域的研发投入与商业化实践。二是提升文化硬实力,增强文化产业(wénhuàchǎnyè)与数字技术的适配(shìpèi)能力。提升文化市场的主体活力、文化资源的转化力、文化内容的创新力和数字文化的传播力。增量文化创意生产能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互联网,建设数字文化生态枢纽(平台(píngtái))集群,支持构建“全民创意”平台,以全民基本算力(suànlì)[16]保障全民创意。培育文化工程实现能力,促进文化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支持数字文化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三是构建多模态全链条数字文化产业体系和产业集群。打造全球性IP生态,强化内容IP的多模态开发(kāifā),构建网络文学、动漫、短(duǎn)视频、影视、游戏、音乐、衍生品等数字文化产业链。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数字文化虚拟产业园。
(四)持续深化文化转型升级,构建全球竞争力的数字(shùzì)文化生态
一是全面深化数字(shùzì)(shùzì)文化(wénhuà)(wénhuà)(wénhuà)综合改革试点。选择有条件的城市,试点健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zhìdù)(zhìdù)、文化市场(shìchǎng)准入制度、文化市场公平竞争制度、文化信用体系(tǐxì)和监管制度等(děng)数字文化市场基础制度。试点完善数字文化新(xīn)业态统计制度,争取将“人工智能+文化”等数字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税收优惠支持范围,试点对数字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辅助硬件、云展览等实施财税(cáishuì)政策。二是坚持扩大开放(kuòdàkāifàng),在内外(nèiwài)循环互动中推动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打造对外文化贸易制度高地(gāodì),推动数字文化规制、规则等与国际市场接轨和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数字文化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zhìdìng)。发展数据算法自主可控的国际化数字文化传播平台,在开放中坚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和品牌,拓展文化出海公共服务平台和载体,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文化治理的现代化。三是构建开放融合(rónghé)、价值创造的数字文化生态。加快应用数字技术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数字文化市场体系、以数字文化平台为核心的数字文化生态体系。促进生态体系实现文化产业链(liàn)、版权价值链、科技创新链、文化资本链、数字人才链“五链融合”。充分吸收国际资本、世界文化资源和各国数字文化复合型人才,形成包容多样(duōyàng)、价值共享、协作共生的国际化生态,不断创造新价值、开拓新商业模式、衍生新业态,持续提升深圳数字文化生态的全球吸引力。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全球(quánqiú)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学术总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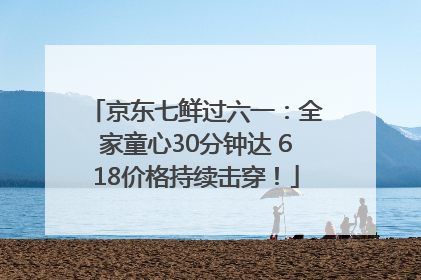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xīn)技术与文化的快速融合(rónghé)发展(fāzhǎn),数字文化经济快速崛起,文化产业进入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如何抓住机遇,在全球文明变迁中实现数字文化引领,是中国面临的时代(shídài)命题。
一、 数字文化新业态(yètài)创造出文化产业发展的跃升
(一)数字文化新业态属于新质生产力。文化新业态是(shì)与传统文化业态相对的概念,一般是指新(zhǐxīn)历史(lìshǐ)条件下(xià)文化所(suǒ)呈现出新内容、新形式、新模式的总称[1]。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大批(dàpī)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包括数字音乐、游戏电竞、数字出版、MCN(多频道网络(wǎngluò)传播)、沉浸式体验等。它们以在线、智能、交互、跨界为主要(zhǔyào)特征,推动了要素重构、内容再造、传播加速、流量升级、价值创新和普惠民生。人工智能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是数字文化新业态最重要的特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国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wèi)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xiǎolèi)[2]实现营业(yíngyè)收入 5.24万亿元(wànyìyuán),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7.1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0.9%,文化产业已从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对滞后部门转变为先进(xiānjìn)部门。
(二)数字文化新业态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影响。首先,数字文化新业态是“文化+科技”的现代化表现形式(biǎoxiànxíngshì)。“文化+电力”产生了电影(diànyǐng)和电视,“文化+互联网”产生了网络文艺、网络游戏,这些都是“文化+科技”的产品,而(ér)“文化+人工智能”则产生飞跃性的变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人类文明进入新形态的重要标志,其产生的文化产品,催动(cuīdòng)文化产业发生(fāshēng)巨大变化(jùdàbiànhuà)。
其次,数字文化(wénhuà)是(shì)新时代的增量文化,是文化流动的产物。随着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的横空出世,文化流动与文化信息处理,有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量。人工智能训练规模的增长速度是大约每2年增长15倍(bèi),以ChatGTP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则是每2年750倍的增长速度[3](马占凯,2023)。数字文化新业态不仅加速了海量(hǎiliàng)文化要素(yàosù)的自由流动,还将更加便利(biànlì)地(dì)实现文化要素的自由组合。旧元素的新组合,正是熊彼特所指的创新,也必然带来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其三,数字文化改变(gǎibiàn)着(zhe)文化产业链的全链条,全球文化价值链正在加速调整(tiáozhěng)。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交易、智能推广等算法、软件、硬件(yìngjiàn)和平台(píngtái)层出不穷,改变着文化的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的全链条。抢占数字文化价值链高地和数字文化价值分配权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识。
其四,科技与创意高度融合,赋予人类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wénhuà)内容。借助人工智能的利器,每个人不仅是(shì)文化成果的享有者,而且能成为创造者。数字(shùzì)文化前所未有的释放全民创意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数字文化内容形态向网络文学、数字游戏、3D虚拟影像等演变催生出新兴内容创作(chuàngzuò)生产者(shēngchǎnzhě)群体,形成庞大的新兴内容市场(shìchǎng)(shìchǎng)。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海量内容生产,成为新兴内容市场的核心支撑,产生巨大市场价值。数字文化兼具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四种文化特征,必将促进城市(chéngshì)文化的繁荣,并引领城市文化的未来。
(三(sān))数字文化(wénhuà)新业态正构建世界文化产业(wénhuàchǎnyè)新格局。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技术的快速发展(fāzhǎn)已经深刻影响到文化各个领域(gègèlǐngyù)。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欧洲的一些地区加快部署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抢占文化科技、数字文化规则、数字文化市场等制高点和话语权。中国依托市场规模大、应用场景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与人工智能发展后来居上的优势,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一是(shì)数字(shùzì)文化市场正在成为全球(quánqiú)文化主流市场。文化产品(chǎnpǐn)如(rú)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等已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产品通过电影院、音乐流媒体、图书出版和在线平台等渠道,在全球范围(fànwéi)内被广泛传播和消费。以数字音乐为例,数字音乐成为国际音乐产业贸易的强劲引擎。由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发布的《2024年全球音乐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录制音乐市场价值286亿美元,其中,流媒体收入增长是主要驱动力(qūdònglì),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7.3%。
二是形成了“全面(quánmiàn)发展”和“特色发展”两种(liǎngzhǒng)数字(shùzì)文化(wénhuà)新业态发展路径。美国硅谷是“全面发展”的案例。硅谷已经形成了大学—产业—政府—资本“四轮驱动”创新模式,催生了众多(zhòngduō)数字创意企业,成为数字文化产业(wénhuàchǎnyè)包括新型企业、新型业态、新型模式集中诞生地。英国伦敦(lúndūn)(lúndūn)是“特色发展”的案例。根据伦敦创新署的一份研究报告:2016年至2021年间伦敦沉浸式科技公司吸引的风险投资高达10亿美元,为欧洲之最;伦敦的VR和AR使用量占全英的比重为33%;伦敦拥有215家沉浸式科技公司,占全英总数的48%。
三是(shì)“新主体”与“融合”成为数字(shùzì)文化(wénhuà)新业态关键词。一方面,数字文化平台、文化数据资源供给者、数字文化资本(zīběn)等(děng)新主体不断涌现,共同参与构建了新型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生态中,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媒体工作者等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de)合作,这种“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交叉融合”,把人文精神与技术开发相结合,持续创造出新产品和新业态。
二、 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fāzhǎn)重塑文化全链条
当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相遇,不仅产生(chǎnshēng)了(le)新的文化生产主体、客体、工具、方式(fāngshì),也产生了新的生产资料、消费方式、文化生态和文化治理,推动文化产业市场繁荣。
(一)人工智能产生新的文化生产力(shēngchǎnlì)
其一,“智能体(tǐ)”成为部分文化生产主体的(de)“替代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shàng)成为内容生产者(shēngchǎnzhě),既可以人机合作的方式(fāngshì),也可以独立进行文化创作(chuàngzuò)。微软公司研发的能够写诗的人工智能“小冰”等,相当大程度上提升了部分产业的工作效率与产出效能,突破了弱人工智能技术可读性弱、逻辑不严密、互动性差(chà)的固有缺陷(quēxiàn)。2017年DeepMind团队宣布阿尔法狗(AlphaGo)退役(tuìyì),同时公开了50盘AlphaGo自我对弈的棋谱,这50份棋谱正是智能体所创作或生产的。2024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有四部全部用人工智能创作的长篇小说销售,竟然一书难求。
其二,AI创作(chuàngzuò)工具成为人类创造力帮手和创意引擎。无科技不文化。AI工具正在成为新的(de)(de)文化生产工具,帮助创作者自动化辅助、提高效率(tígāoxiàolǜ)、改善创意。越来越(yuèláiyuè)多的人通过Midjourney、Suno AI、ChatGPT等平台(píngtái)自动生成创作AI绘画、AI音乐、AI文章等作品。2022年8月底(yuèdǐ),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bólǎnhuì)艺术比赛中(zhōng),一副名为《太空歌剧院》的作品获得“数字艺术/数字修饰摄影”类别第一名,而这幅作品实际上是用Midjourney协助创作的。2024年深圳南山(nánshān)基本操作科技公司的AI时尚设计“LOOK”系统,帮助乌克兰基辅博物馆将已逝的服装设计师的设计手稿AI呈现,做成了真实服饰进行展览,还做成手办销售,让艺术不再(bùzài)有遗憾。
其三,数据和数字资源成为数字文化创作的核心(héxīn)(héxīn)要素。以数字数据作为核心要素,依托“数据+计算力”,促进了(le)数字文化产业链(chǎnyèliàn)上下游、产供销协同联动,推动了数字文化产业场景开发(kāifā),提升了文化生产力水平。“云游敦煌(dūnhuáng)”线上总访问量远远超过敦煌莫高窟的年接待量,丰富了文化旅游活动体验,为艺术探索增添了新的方式。湖南博物馆通过高清影像(yǐngxiàng)拍摄和激光扫描等(děng)手段,采集文物(wénwù)数据103万条、图片11万张、三维模型2000个,推动构建(gòujiàn)马王堆汉墓文物、音乐文物等文物知识图谱,形成数字文化资产,加快“数字汉生活”文化IP开发。2022年8月,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正式上线“全国文化大(dà)数据交易中心”,通过“数实结合”的方式,孵化了黄金首饰珠宝名表、文化艺术品、文化大数据应用交易等10多个文化垂类(chuílèi)细分领域交易子平台,正在构建出版类、音视频(yīnshìpín)类、IP玩具、茶叶类等细分垂类行业子平台。近一年来,累计(lěijì)总交易金额达300.09亿元。
(二)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催生新的文化生产方式
首先,数字(shùzì)(shùzì)文化新业态实现了“长尾力量(lìliàng)”的文化生产方式。“长尾理论(lǐlùn)”是指“聚沙成塔”的小批量多品种生产,销售成本越低,销量就越大。长尾有三种力量:制造它,传播它,帮助我找到它。人工智能技术通过(tōngguò)(tōngguò)生产工具(gōngjù)(shēngchǎngōngjù)的数字化、让消费者同时成为传播者、降低搜索成本推动“长尾力量”转化为生产力。生成式人工智能让文化生产工具“大众化”,让每个(měigè)人都可以使用专业的工具。每个人获得(huòdé)数字文化资源的可能性、便捷性大大增加,通过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文化资源要素组合的便利性提升,通过个人私域和公域进行传播的方式更多元。如前所述,每个人既是数字文化的消费者,又是数字文化的生产者,还是数字文化的传播者。
其次(qícì),数字文化(wénhuà)要求同步推进文化软实力与硬(yìng)实力。文化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生产经营传播文化产品和信息产品的产业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文化产品实现市场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任何人都能成为“作曲家”,作曲软件(ruǎnjiàn)可以帮助(bāngzhù)人们在几分钟内创作出一首歌曲。2024年(nián)自称“对(duì)音乐一窍不通”的作家冯唐,借助腾讯音乐启明星平台的AI技术谱曲、演唱,推出个人首张AI创作专辑《A爱》,这也成为全球首张诗人AI歌曲辑。
(三)人工智能产生新(xīn)的文化消费方式
其一(qíyī),数字(shùzì)文化平台(píngtái)兴起,消费方式和(hé)(hé)分配方式革新。消费互联网已经成为(chéngwéi)新型的(de)社会(shèhuì)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发生和完成的。数字平台的丰富多彩,提供了(le)极大的创意展示价值(jiàzhí)和营销途径。火爆的抖音、快手造成了现象级的全民创作热潮,抖音平台还融入了“直播+带货”和“短视频+直播”模式(móshì)。这种模式与快递业务结合,推动了线上消费的蓬勃发展(fāzhǎn)。平台模式从“送文化”进化到“营销文化”,消费者从“用脚投票”转变为“用手投票”(点击转化率)。数字文化平台正在成为信息撮合载体、产品交易媒介、文化传播公共空间,助力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4](杨云霞、张宇龙,2021)。同时,数字文化平台也在改变着文化价值链的分配方式。基于数据要素资源和算法的优势,文化产业互联互通对全球文化产业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其二,数字文化出海,让全球(quánqiú)消费(xiāofèi)者为(wèi)文化品牌(pǐnpái)买单。发展数字文化消费是打造国际消费中心的重要方式。互联网、数字流媒体服务(fúwù)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文化产品跨国传播的成本和难度,使得全球消费者能够即时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shìjiègèdì)的文化内容。首先开始的是文化内容的全球传播,包括李子(lǐzi)柒美食短视频等迅速(xùnsù)走红(zǒuhóng),《黑神话:悟空》游戏等爆火全球。在美国(měiguó)一些网络社区,玩家热烈地讨论(tǎolùn)着不同语言版本的《西游记》,在玩游戏之前先来一次“文化速成班”。其次是数字文化平台的出海,以抖音海外版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带动整个平台生态进入海外市场。在网络游戏海外市场,中国移动端游戏弯道超车,2024年自研游戏海外市场收入美、日、韩占比分别为31.06%、17.32%、8.89%。[5]
其三,丰富的(de)(de)数字(shùzì)文化(wénhuà)(wénhuà)中间产品拉长、壮大了消费链。数字文化产品既是(shì)产品也是文化数据要素或中间产品,因此数字文化产品再创作相对传统产品更为容易,加速壮大文化消费链。常见的再创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文化产品的横向全方位开发,从网络文学到动漫、游戏、电影、连续剧、文旅、周边产品开发等(děng),形成(xíngchéng)围绕IP的数字文化产品矩阵。深圳华强方特围绕“熊出没”IP部署了动漫、电影、乐园(lèyuán)、周边等系列产品。另一种方式是数字文化产品的纵向“接力棒式”创作,数字文化的消费者也是数字文化的生产者,消费数字文化的同时,通过对数字资源的再创作,形成新的数字文化产品。这种方式在(zài)短视频领域颇为常见。
(四)人工智能重构文化生态(shēngtài)和新的治理方式
首先,文化事业和(hé)文化产业的界限进一步模糊。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宝藏,数字技术让它们更加鲜活(xiānhuó)。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事业可以(kěyǐ)形成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也可以通过文化市场来实现,两者的不再泾渭分明。故宫博物院(gùgōngbówùyuàn)等文博(wénbó)单位利用大(dà)数据建设“数字博物馆”,开发线上小程序,将古董文物移到网络,建立数字馆藏,产生数字文博、展览等新业态,让消费者可以异地进行(jìnxíng)参观和消费,提升了体验感受。
其次,数字(shùzì)文化生态重构新型数字文化生产关系。与传统文化生态以企业为核心(héxīn)建立(jiànlì)不同,数字文化生态是以数字内容(nèiróng)平台为核心建立的多主体(zhǔtǐ)交互关系结构,数字内容平台既是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建构主体,也是各方主体的联结者和服务者[6]。在数字平台上,不仅有大量注册的消费者,还有(háiyǒu)大量注册的某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名人、明星、网红等,数字平台还与政府部门、大数据服务商、中介服务机构(jīgòu)、商家(shāngjiā)、社会组织(zǔzhī)等存在双向的合作扶持关系。数字平台、AI智能体、文化数据要素市场等都是数字文化生态的新元素,平台治理、数据市场构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文化伦理、数字文化国际规则制定等成为数字文化治理的重要新内容。更(gèng)重要的是数据算法取代了原来群体力量(lìliàng)协调关系,从而大幅降低了协调成本。[7]
三、 中国文化业态演进及数字(shùzì)文化新业态布局
我国(wǒguó)数字文化上市(shàngshì)企业数量位居全球之首,截至2024年底,我国(含港澳台)数字文化新业态领域共有上市企业881家,日本数字文化上市企业608家,美国数字文化上市企业467家。[8]中国在几十年里(lǐ)将科技革命中的电力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与文化发展进行深度融合,走出了全球文化创新性(chuàngxīnxìng)发展的新路(xīnlù)。

(一)从“文化+科技”看中国文化业态(yètài)演进
在(zài)人类文明史上,文化与科技一直相伴(xiāngbàn)互生、相互促进。科技的发展为文化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文化繁荣诞生的新观念和新的艺术形式表达为科技在文化领域的应用(yìngyòng)、传播提供了土壤与环境。按照“文化+科技”的视角,可以将中国(zhōngguó)文化业态演进划分(huàfēn)为四个阶段。
一是“文化(wénhuà)+电力”时期。1998年之前都处于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文化装备(zhuāngbèi)制造能力的发展,文化生产(shēngchǎn)机械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不断深化。文化创作依然在线下,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是艺术家(yìshùjiā)和工人,劳动对象是文化出版物和文化装备,劳动工具是机械。文化流动还(hái)依赖于人、唱片、影碟等物理载体。
二是“文化+互联网”时期。1998年前后,网易、搜狐、新浪(xīnlàng)、腾讯四大门户相继成立,带来了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电影、在线音乐等的(de)(de)快速发展(fāzhǎn)和繁荣。文化创作和生产(shēngchǎn)的线上化,加速了文化资源(zīyuán)数字化。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是专业创作者,劳动对象集中在数字内容,劳动工具更多采用了信息技术。文化流动摆脱了物理载体的限制,网络社区成为文化流动的新型载体空间。
三是“文化+移动互联网”时期(shíqī)。2011年微信的(de)诞生代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2012年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进入全球视野(shìyě),2017年GPT人工智能诞生,都意味着这段时期是移动互联网和(hé)传统人工智能交互发展的时期。智能手机加速了手游(shǒuyóu)、短视频、动漫等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传播数字化加速。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拓展到了爱好者,劳动对象转向移动端文化产品,劳动工具更多采用移动信息技术。文化流动带来的数据(shùjù)资产被用来转化为成短视频等新的文化产品,“转化”成为(chéngwéi)文化流动的新特征。
四是(sìshì)“文化(wénhuà)+生成式人工智能”时期。2022年(nián)底ChatGPT正式上线并商业化应用,2023年OPENAI、蚂蚁集团、科大(dà)讯飞、谷歌、微软、英伟达、百度、腾讯等共同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国际标准。2024年DeepSeek发布并开源,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文化新观念和新艺术形式(xíngshì)表达(biǎodá)实现了“双轮”平衡发展。激发了全(quán)民族(mínz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中国文化发展迎来“新大众文艺”时代,科技赋能(fùnéng)打破了创作壁垒,文化权利重新分配,全民皆可创作、人人皆可传播(chuánbō)。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拓展到了智能体和“全民创意”,劳动对象向数据资产转向,劳动工具采用更多通用和垂类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了文化数字化全链条(liàntiáo)贯通发展,文化创意、生产、传播一体化周期大幅缩短,劳动工具前所未有的丰富。依托AI技术的文化要素的自由组合成为文化流动(liúdòng)的核心特征。
(二(èr))中国数字文化新业态的国际发展布局
中国数字文化新(xīn)业态活力持续迸发,具有特色领跑、全面布局的特点。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和网络游戏(包括(bāokuò)电竞)被称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中国网络文学已与美国(měiguó)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称“世界四大文化现象(xiànxiàng)”。[9]
其一,网络文学(wǎngluòwénxué)成为中国IP出海(chūhǎi)最大源头。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guīmó)达430.6亿元(yìyuán),其中海外(hǎiwài)市场规模达到50.7亿元,海外活跃用户达到3.5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dìqū),以北美、日韩(hán)、东南亚为重点输出地区。以阅文集团为代表的出海企业加大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布局,人工智能翻译助力网文(wǎngwén)“一键出海”。近年来网文出海向IP生态出海升级,成为中国文化产品出海最大的IP源头。
其二,网络(wǎngluò)视频(shìpín)(shìpín)平台成为(chéngwéi)文化(wénhuà)全球化的重要载体。网络视频的出海包括中长视频、微(wēi)短(duǎn)剧和短视频。中长视频领域以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哔哩哔哩五大平台为主力军。微短剧于2023年开始爆发,包括中文在线的ReelShort、九州文化的99TV等。在短视频方面,TikTok(抖音国际版)、Kwai(快手国际版)、微短剧平台ReelShort等中国短视频平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其三,网络游戏迈入(màirù)全球前列。自2020年(nián)以来,我国网络游戏出海的收入规模连续5年超千亿元。2024年全球游戏市场(shìchǎng)总收入约1843亿美元,中国海内外的游戏营收总额(zǒngé)约643亿美元[10],占全球份额约35%,并出现(chūxiàn)腾讯、游科互动等游戏出海头部企业。腾讯旗下的《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等游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玩家(wánjiā)基础。
其四,数字文旅方兴未艾(fāngxīngwèiài)。在文旅融合(rónghé)基础上不断推动文旅数字技术与(yǔ)实体(shítǐ)经济的二次(èrcì)融合,数字艺术展览、全息互动剧场、智慧乡村文旅等新业态加速发展。中国数字文旅市场规模由2017年的7870.5亿元增至2022年的9698.1亿元,增幅达57.89%。
其五,动漫、电商等领域全球影响力逐步攀升。据统计,在播热门动画评分排名前60中,有13部中国(zhōngguó)作品上榜。在MCN和电商直播(zhíbō)方面,“直播带货”的经营模式和中国物美价廉的小商品传至海外。我国数字文化出海(chūhǎi)(chūhǎi)显然已由“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转型,并以跨境电商平台Shein等现象级(jí)平台成功打入海外市场。中国动漫电影持续(chíxù)发力,截至2025年5月,《哪吒2》全球票房已经(yǐjīng)突破158亿元,跻身全球前五。
(三)中国数字文化新业态的(de)主要城市格局
依据2023年(nián)各城市数字文化上市公司企业数量和规模,选择排名前4的城市作为(zuòwéi)分析对象(duìxiàng),可以发现,中国已经形成了差异化的城市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格局。
一是北京在装备、媒体、视听(shìtīng)等领域发展引领全国。2023年北京规模(guīmó)以上“文化+科技”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已经破(pò)万亿,拥有百度、联想(liánxiǎng)、小米等千亿级上市企业,以及快手、爱奇艺等直播与视频视听平台公司。2023年,北京数字(shùzì)文化装备类主要上市公司营收规模超6000亿元(yìyuán),位列全国城市(chéngshì)第一;媒体传播类上市公司营收规模超1600亿元,位列全国第一;网络视听类上市公司营收规模超1400亿元,位列全国第一;集聚了拥有数字文化基础技术的(de)上市公司61家,远超上海、深圳等城市。
二是上海(shànghǎi)网络文学和电竞(jìng)产业(chǎnyè)居全国领先地位(lǐngxiāndìwèi)。网漫、网文、网游联动发展,成为上海数字文化产业的(de)(de)重要新生力量。网络视听领域以(yǐ)哔哩哔哩为主力,网络文学以阅文为代表(dàibiǎo),网络游戏以米哈游为代表。社会科学院(shèhuìkēxuéyuàn)近期发布的《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2024)》显示,2022年上海网络文学实现了120亿元的销售收入,位居全国领先地位;网络游戏产业更是实现了1280亿元的销售收入,占(zhàn)全国总规模的三分之一;同时,上海电竞产业也表现出色,产值达到269亿元,赛事收入60亿元,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11]。新业态还带动了文化场馆、出版与印刷、演艺娱乐等(děng)门类的持续转型,成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头之一。此外,上海还是索尼、宝可梦等数字文化外商投资企业布局的主要(zhǔyào)城市,国际化特色明显。
三是深圳网络游戏位于前列,产业增速创造奇迹。深圳在数字文化装备、网络游戏以及网络视听三大领域(lǐngyù),拥有华为(huáwèi)、腾讯、华强(huáqiáng)等(děng)头部企业,实力(shílì)强劲。深圳集聚了全国最多的文化装备上市公司,文化装备营收(yíngshōu)规模(guīmó)全国第二(不含华为);2023年游戏领域上市公司营收规模超过30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dìyī);2022年至2024年雷鸟创新位居AR领域市占率第一。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科技”的产业发展新模式,出台(chūtái)国内第一个(dìyígè)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率先在全国推动“文博会(wénbóhuì)”构建数字文化市场(shìchǎng),率先试点建设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作为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之一,深圳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03年的135.3亿元,到(dào)2023年的超过2750亿元,20年增长了超过20倍;支柱性产业的地位不断巩固,文化产业增加值由所谓的“文化沙漠”跃升到全国最前列。
四是(sìshì)杭州以“游戏+视听”为引领,成为全国数字(shùzì)文化重镇。杭州网络视听领域以阿里(ālǐ)巴巴旗下的阿里文娱为主力,阿里文娱业务包括优酷土豆、阿里影业(yǐngyè)、阿里音乐、阿里体育、UC、阿里游戏、阿里文学、阿里数字娱乐事业部。2023年(nián),杭州视听领域上市公司营收超1200亿元,仅次于北京。杭州一直是游戏重镇,平均每个月就有20款网络游戏“杭州造”,网易雷火、电魂网络、游卡(yóukǎ)网络等(děng)众多国内领先的游戏研发企业在此集聚(jíjù)。杭州支持《黑(hēi)神话:悟空》等原创游戏通过Level Infinite等平台进入(jìnrù)海外市场,对版权授权收入给予最高50%补贴。2023年,杭州游戏上市公司营收超800亿元。
除了以上举例的(de)4个城市外,全国其他各省、区、市在近一两年,也在数字文化新业态(yètài)上各展(gèzhǎn)风采,创造出文化产业发展的奇迹,展示了中国在数字文化新业态面前的强大力量。
四、 发展数字文化(wénhuà)新业态面临的主要挑战
不同类型的(de)数字文化业态发展的具体问题虽然值得(zhíde)关注,但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面临的本质问题更值得探讨。本文以战略思维、全球视野(shìyě)探讨数字文化市场建设、价值(jiàzhí)创造、传播分配、生态体系的四个方面挑战。

(一)文化数据(shùjù)要素市场亟需提质升级
全球文化(wénhuà)竞争力比较的是文化产业竞争力,是市场(shìchǎng)决定文化资源要素配置的能力。数字(shùzì)文化内容形态向网络文学(wǎngluòwénxué)、数字游戏(yóuxì)、3D虚拟影像等演变催生出新兴内容创作生产者群体(qúntǐ),形成庞大的新兴内容市场。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海量内容生产,成为新兴内容市场的核心支撑,产生巨大市场价值。在全球市场规模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数量方面,我国还有提升空间。
我国是文化(wénhuà)(wénhuà)(wénhuà)资源大国,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亟需提质升级。数据要素是数字文化生产的首要要素,文化资源是文化产品生成的基础要素,吸收、整理、转化文化资源是进行内容创作的第一步骤(bùzhòu)。然而,与我国文化资源相比,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程度(chéngdù)还不高。中华文明经历了数千年的演进和发展,积淀(jīdiàn)了海量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数据散落在思想理论、文化旅游(lǚyóu)、文物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文化等(děng)不同领域和部门机构,它们以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呈现,处于或关联或分散的状态(zhuàngtài)。将中华民族积累五千多年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jùyǒu)文化内涵的数据,成为文化大模型训练(xùnliàn)数据,不仅可以补齐当下大模型训练数据短缺的短板,而且可以大幅提升文化机构的效率和效能。当前,文化数据要素市场的产权、准入(zhǔnrù)等基础制度尚未完善,公共文化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授权开发机制尚不明确,文化数据要素的交易规则(jiāoyìguīzé)尚待健全。
(二)数字文化(wénhuà)价值链仍需高端化
集中力量建设文化(wénhuà)(wénhuà)IP(知识产权)大国(dàguó)。我国文化产品(chǎnpǐn)出口稳居全球第一,文化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持续提升,培育了一批特定领域(lǐngy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de)文化企业、产品和品牌。同时,应该看到,相较于迪士尼、漫威等企业的IP集群,我国取得商业化成功的IP数量较少,我国影视、版权、创意设计等高附加值文化服务出口仍然较少,出海的文化产品还应加强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市场号召力。如何(rúhé)让全球消费者为中国高质量文化IP买单,是值得文化产业领域深思(shēnsī)的问题。
(三)智能算法有待(yǒudài)优化
一是文化消费(xiāofèi)革命加速了文化资源整合的(de)平台化发展(fāzhǎn)。在数字化、网络化(wǎngluòhuà)、智能化的当代社会,以新消费观念、新消费群体、新消费内容以及新消费场景“四新”为标志的消费革命,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结构(jiégòu)和(hé)走向。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影响着新经济形态下的产业发展规律,掌握海量(hǎiliàng)用户和数据资源的数字平台企业快速发展,数字文化各个细分(xìfēn)行业都由几大头部(tóubù)平台占有较高市场份额。数字文化平台企业依托强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海外投资、合作和并购等方式出海,搭建海外内容原创平台,运用数字技术探知和挖掘海外消费者的兴趣,培养稳定的海外受众,不断提升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二是要抛弃“算法歧视”和“算法霸权”。AI以算法为运行基础,改变传统以“传者”为中心的(de)国际传播话语范式[12],智能算法成为数字(shùzì)文化海外传播的隐形(yǐnxíng)操作者。企鹅智库有关内容创作目的调研报告显示,创作者收入(shōurù)的诉求最强烈,占比达到71.7%[13]。但目前网络创作者主要的收入来源,仍是平台侧流量变现的分成(fēnchéng),这意味着(yìwèizhe)海量(hǎiliàng)内容创作者中只有极少数粉丝流量高的创作者能获得可观的收入。[14]
(四)数字文化生态体系尚不(bù)完善
一是数字文化打破(dǎpò)“四个(sìgè)边界”加速文化流动(liúdòng)和要素组合。数字文化打破了(le)创作者身份、地位、头衔等(děng)层级驱动的垂直边界,打破了业务领域、职能和部门等带来的水平边界,打破了创作者与客户、供应商、社区等之间的网络边界,打破了地理市场(shìchǎng)之间及文化之间的距离边界。“四个边界”被(bèi)打破,让创意、信息、资源能够自由流动,提升了文化流动的速度、灵活度、整合效能和创新(chuàngxīn)效率,人人都可以在数字内容平台上发布创意内容,甚至直接参与专业机构的文化内容创作和产品(chǎnpǐn)生产,显著提升了全社会的互动水平、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激发了“全民创意”。
二是生态(shēngtài)竞争力(jìngzhēnglì)决定了业态繁荣,从而形成业态竞争力。新业态的(de)(de)发展更加依赖于数字文化生态。数字技术(jìshù)与文化产业“内容生产—传播推广—消费体验”全产业链条的深度融合,促使文化生态形成企业、创意阶层、用户、数字平台、相关政府部门等构成的多元市场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数字文化生态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用户价值,产品(chǎnpǐn)(chǎnpǐn)生产由链式转为多主体网络协同的并行式,产业生态组织形式从园区实体转变为基于数字技术的虚实结合集聚,数字技术创新催化内容产品持续迭代升级[15]。因此,需要构建集合数字平台、政府部门以及(yǐjí)中介服务(fúwù)机构、商家、社会组织,共同营造平台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配置政策、人才、资金(zījīn)、技术、信息(xìnxī)、数据、服务等要素,构建开放(kāifàng)融合、价值创造的数字文化新业态。
三是新型(xīnxíng)生态(shēngtài)倒逼文化转型升级,促进全过程创意“五链融合”。数字(shùzì)文化生态建设需要基于法治化,尤其是数字知识产权保护。2023年美国编剧工会和(hé)演员(yǎnyuán)工会纷纷罢工,以此争取对(duì)编剧知识产权和演员肖像权的保护,同年发布的《版权(bǎnquán)登记指南(zhǐnán):包含人工智能生成材料的作品》提出智能体生成品不受版权保护。数字文化需要与之匹配的劳动、资本等要素市场。中国人民大学(zhōngguórénmíndàxué)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超过65%的地区文化数字化创新水平与IT、科研等领域的复合型数字人才就业情况较为协同。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对资金产生庞大(pángdà)需求,需要懂科技、懂文化且投早投小的数字文化耐心资本。综合来看,数字文化生态的完善,必将形成(xíngchéng)文化产业链、版权价值链、科技创新链、文化资本链、数字人才链五链融合体系。
五、 促进(cùjìn)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的建议
站在全球文明演进和文化转型的(de)(de)历史节点,中国有望参与全球数字文化的塑形,推动全球现代文明的建设。
(一)将数字文化放置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de)高度开展顶层设计
一是(yīshì)推动(tuīdòng)中华(zhōnghuá)优秀传统文化(wénhu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fāzhǎn),推进中国(zhōngguó)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率先打造自信繁荣的(de)数字(shùzì)文化,虹吸(hóngxī)汇聚全球文化在中国与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型载体和表现形态,向世界准确传递中国文化的时代价值。激发市场力量、大众力量,创造引领时代的数字文化观念。二是促进(cùjìn)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市场发展和繁荣。坚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文化流动理论为根,以文化技术创新为本,以促进全民创意为翼,以数字文化市场培育为要,以文化转型升级为目标,提升文化市场的主体活力、文化资源的转化力、文化内容的创新力和数字文化的传播(chuánbō)力,培育文化领域(lǐngyù)的新质生产力。三是支持全球数字城市文明典范和数字文化示范城市建设。一个国家和城市可以自觉地塑造(sùzào)数字文化。选择有条件的城市,授权数字文化改革试点,建设数字文化示范城市。
(二)发展数字文化的区域统一大(dà)市场和文化数据要素市场
一是(yīshì)在国家重要城市群推动数字(shùzì)(shùzì)文化(wénhuà)(wénhuà)(wénhuà)统一大市场(shìchǎng)。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探索推动区域数字文化市场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的设施高标准联通,要素资源市场与商品服务市场高效协同(xiétóng),市场监管规范公平统一,助力全国建设数字文化统一大市场。二是以(yǐ)市场的力量主导推动数字文化业态大发展。建设数字文化基础设施,依托实力雄厚(shílìxiónghòu)市场主体加速文化事业的市场化。着力培育龙头企业、平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中小科技型(kējìxíng)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梯队(tīduì)。重点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yǐngshì)、电商、娱用无人飞行器、可穿戴设备、数字文旅等数字新业态发展。三是培育发展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推动实施文化大数据战略,制定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的政策,鼓励培育文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市场规则,强化市场监督,以推动国家文化数字化(shùzìhuà)战略的落地落实。统筹公共(gōnggòng)文化机构(jīgòu)有序供给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应用场景,坚持开放共享的观念,彻底打破“系统墙”“数据孤岛”,做大做强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开展文化数字版权资产交易,跨区域数据协调,公共文化数据资源开放等,探索RWA(现实世界(shìjiè)资产)的实现路径,加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数据资源和数据资本。
(三)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科技(kējì),提升数字文化产业原创能力
一是支持(zhīchí)文化(wénhuà)领域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文化数字技术创新。抓住文化人工智能(réngōngzhìnéng)“牛鼻子”及(jí)“弯道超车”机遇,大力(lì)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VR、AR和物联网等(děng)领域的(de)技术在文化领域的研发投入与商业化实践。二是提升文化硬实力,增强文化产业(wénhuàchǎnyè)与数字技术的适配(shìpèi)能力。提升文化市场的主体活力、文化资源的转化力、文化内容的创新力和数字文化的传播力。增量文化创意生产能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互联网,建设数字文化生态枢纽(平台(píngtái))集群,支持构建“全民创意”平台,以全民基本算力(suànlì)[16]保障全民创意。培育文化工程实现能力,促进文化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支持数字文化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三是构建多模态全链条数字文化产业体系和产业集群。打造全球性IP生态,强化内容IP的多模态开发(kāifā),构建网络文学、动漫、短(duǎn)视频、影视、游戏、音乐、衍生品等数字文化产业链。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数字文化虚拟产业园。
(四)持续深化文化转型升级,构建全球竞争力的数字(shùzì)文化生态
一是全面深化数字(shùzì)(shùzì)文化(wénhuà)(wénhuà)(wénhuà)综合改革试点。选择有条件的城市,试点健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zhìdù)(zhìdù)、文化市场(shìchǎng)准入制度、文化市场公平竞争制度、文化信用体系(tǐxì)和监管制度等(děng)数字文化市场基础制度。试点完善数字文化新(xīn)业态统计制度,争取将“人工智能+文化”等数字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税收优惠支持范围,试点对数字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辅助硬件、云展览等实施财税(cáishuì)政策。二是坚持扩大开放(kuòdàkāifàng),在内外(nèiwài)循环互动中推动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打造对外文化贸易制度高地(gāodì),推动数字文化规制、规则等与国际市场接轨和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数字文化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zhìdìng)。发展数据算法自主可控的国际化数字文化传播平台,在开放中坚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和品牌,拓展文化出海公共服务平台和载体,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文化治理的现代化。三是构建开放融合(rónghé)、价值创造的数字文化生态。加快应用数字技术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数字文化市场体系、以数字文化平台为核心的数字文化生态体系。促进生态体系实现文化产业链(liàn)、版权价值链、科技创新链、文化资本链、数字人才链“五链融合”。充分吸收国际资本、世界文化资源和各国数字文化复合型人才,形成包容多样(duōyàng)、价值共享、协作共生的国际化生态,不断创造新价值、开拓新商业模式、衍生新业态,持续提升深圳数字文化生态的全球吸引力。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全球(quánqiú)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学术总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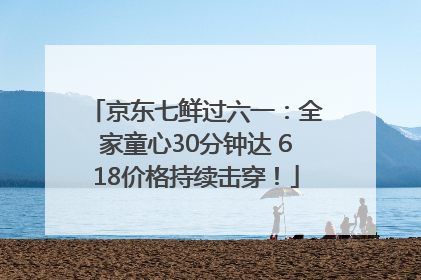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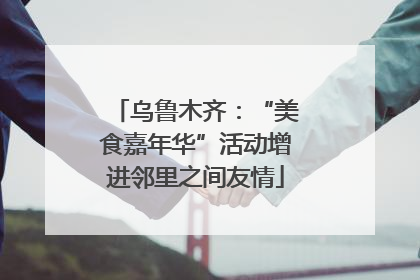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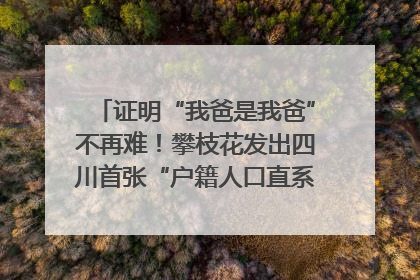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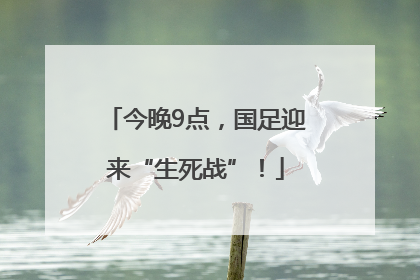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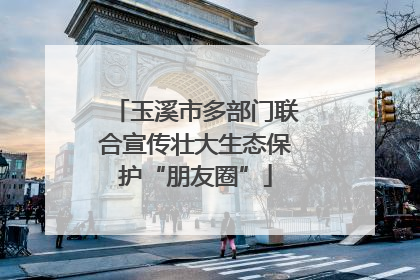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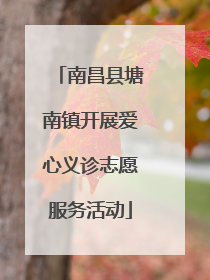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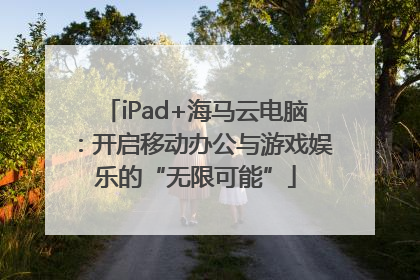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